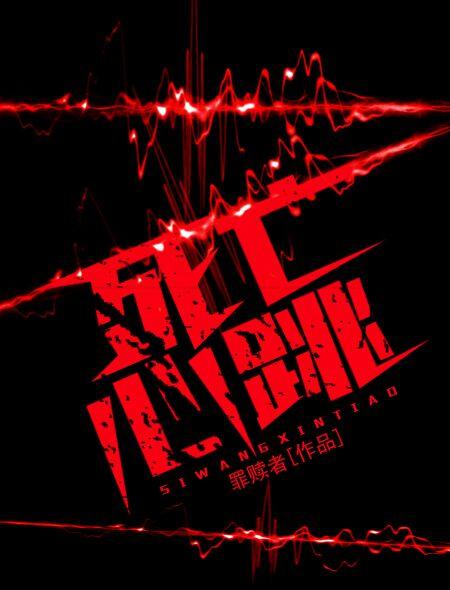顶点小说>嫡女重生之冷峻七王爷免费阅读 > 第38章 闹起来了(第1页)
第38章 闹起来了(第1页)
荣淮张口就要呵斥。
却听荣仪贞话锋一转:
“父亲自荣家起步,走到如今,却比不少有人铺路的世家纨绔子弟前程还要好,可见,那些人若是同父亲一样出身荣家,大抵是拍马也赶不上父亲的。”
“母亲说,父亲才是京中最有真本事的人,让女儿跟在您身边时,多听、多看、多学,哪怕能习得父亲之万一,也够女儿在京中安身立命。”
荣淮的一颗心,随着荣仪贞的话,便如升起、落下、又升起的风筝,上下翻腾。
最后,他万般激动,眉开眼笑,蓄起的胡须都颤了颤,笑道:
“好好好,那为父日后便多教你一些。”
他没想到,从前高傲得像只孔雀一样的郑秋宁,私下里教导儿女时竟也会这般谦卑。
不过也是。
再高傲的孔雀,最后也落在了他荣家的架子上。
自古夫为妻纲才是正理。
女人不管出身如何,只要结了婚,嫁做人妻,都得对夫主崇敬、恭顺,才不算有违伦理纲常。
“只可惜……”
荣仪贞顿了一顿,垂眉耷眼,显出副委屈后悔的样子:
“我年纪太小便失去了母亲,又常年在病中,脾气也不好,竟然忘了母亲的教导,错过了许多和爹爹学习的时间。”
说着说着,荣仪贞就这么低头啜泣起来。
荣淮赶忙上前心疼宽慰女儿,甚至忘了,最开始,他来是要打听叶濯与女儿关系如何的。
父女俩又一起说了好多贴心话,父慈女孝,很是融洽。
荣淮在宁安楼喝了好几盏药茶,等离开时,天已经微微擦黑,快要到晚饭了。
……
晚饭前。
荣仪珠又在荣府花园中见到了荣仪泠。
她惴惴不安,拉着荣仪珠问:“三姐姐,你那个办法到底有几成把握?”
“我一早按照你说的,让人偷来了荣仪贞煮药茶用的壶盖子,用毒水煮了一夜才放回去。”
“你说过,这样做,那毒物便会留在盖中,只等她再煮药茶的时候,毒药会顺着壶盖流到药茶里。”
“怎么如此久了,还是没有那贱人中毒的消息传出来?”
荣仪珠淡定得多。